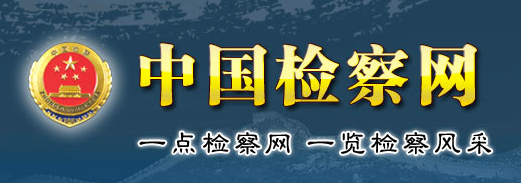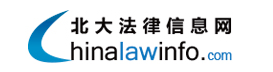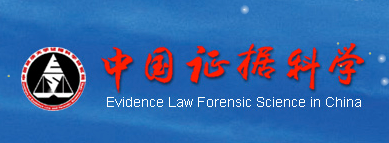韩嘉毅:朱志友故意杀人案辩护词
朱志友故意杀人案辩护词
案情简介
被告人:朱志友,天津市蓟县人,18 岁,农民。
起诉书指控,2001 年10 月6 日下午1 时许,被告人租乘王志民驾驶的出租车回
家,当车行至被告人住处时,二人因故发生口角,被告人从自家院中拿起一把尖刀朝
王志民胸、腹部等处猛捅,又用铁管砸王志民头部,致王志民死亡。被告人将汽车及
王志民尸体弃于京开高速公路北京西红门收费站附近后逃逸,因而犯故意杀人罪。
辩护思路:辩护律师经过对案情仔细认真研究,认为本案没有现场直接目击证人,
从现场勘验的情况、死者受伤及凶器情况、打斗双方的身体条件、年龄和社会经验分
析,被告人致被害人死亡的事实不清,不排除被害人主动侵害被告人、被告人的伤害
行为具有被迫防卫的性质,因此本案定故意杀人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被告人刚
过18 周岁,年龄尚小,有外逃后与家人联系以便返家自首的情节,希望法庭正确认定
案件性质,酌情予以从轻判处。
审判结果:一审和二审法院未采纳律师辩护意见,以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
刑,立即执行。
一审辩护词
审判长、合议庭: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朱志友的委托,指派本所孙毅、韩嘉毅律师做为
被告人的辩护人参加法庭审判活动。辩护人通过查阅案件材料,到第一现场察看,向
公安部资深法医请教后,认为:虽然被告人有伤害的行为,被害人有死亡的结果,但
仅凭目前控方出示的证据材料不能认定被告人犯有故意杀人罪。
一、认定被告人犯有故意杀人罪的证据不足
纵观本案控方出示的全部证据材料,直接指控被告人犯罪的关键证据来自三个方
面,即现场勘查笔录、法医鉴定结论、被告人供述,而这三个方面的证据都不能充分
认定被告人主观上有杀人的故意。以下辩护人将分别针对这三个方面的证据进行分析。
(一)关于现场勘查笔录
辩护人认为:现场勘查笔录,不仅要反映出案件曾经发生,还应通过案发过程中
被告人与被害人在现场留下的痕迹,尽可能揭示案发的过程,通过分析判断,辩别双
方在案发过程中的地位、姿态,从而认定被告人行为的性质、过错程度。本案的勘查
笔录不能起到应起的作用。
首先,本案发生在十月初种麦季节,辩护人了解到案发当天上午刚刚压过麦地,
所以现场勘查像片中双方足迹清晰可见(一组像片表明,对重点足迹已用石膏提取鞋
样)。然而,现场勘查笔录中并没有具体描述现场发现了几双足迹,哪些是旅游鞋(被
告人穿的),哪些是皮鞋(被害人穿的),是哪个足迹在前面跑,哪些足迹在后面追。
没有描述的情况下就存在两种可能,一种是被告人追被害人,另一种是被害人追被告
人。这就必然导致两种合理的怀疑,一是行凶,二是防卫。
其次,现场勘查笔录中对是否有人倒地没有描述。是身材较瘦的被告人倒地,还
是身材较胖的被害人倒地。不同的人倒地同样也可以对被告人行为性质产生两种合理
的怀疑。
总之,用这份现场勘查笔录,作为认定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的主要证据,显然是
不充分的。
(二)关于法医鉴定结论
辩护人曾为此向公安部资深法医请教,通过咨询,辩护人得出该鉴定结论同样不
能作为认定被告人故意杀人罪的结论。
首先,从致伤的数量上。被害人全身三十余处钝器伤、锐器伤,结合被告人所使
用的工具,其任何一件都可以在极少的几次攻击内完成犯罪行为,实现杀害被害人的
目的。在没有合理理由的情况下,为什么要反复攻击被害人后,才致其死亡。
其次,从攻击的部位分布上。1、头部有两处钝器伤,但伤情不重,显然被告人
并没有完全挥动铁管大力攻击被害人头部。从铁管的尺寸、重量及两端有血迹的描述
上,可以看出,以此工具打坏被害人颅骨是相当容易的事情;2、头、脸部有锐器伤,
也不符合故意杀人的特征。用刀杀人通常情况下不会攻击被害人头面部;3、绝大部
分 伤情都发生在被告人正面,这至少表明被害人始终面对,没有逃避。这也表明不
管被告人持有什么样的心态,至少被害人并没有感知被告人要杀他。4、不存在被告
人从后面追杀被害人的情况,否则在被害人的背部将有十分明显的较为严重的伤情。5、
在伤势排列方向上,是多方位、多角度、力度不一的,这些完全符合搏斗过程中致伤
的特点。
再次,在伤情严重程度上,除胸部第1、3、6、7处伤到胸腔,使心肺功能损
伤外,其余大多数皆为表浅伤。这就产生了两种可能判断,要么被告人不想使对方伤
的很重,要么被告人无法伤到被害人。显然后面的情况是不可能的,因为两个人在现
场留下搏斗的痕迹。
总之,被害人身上的伤情,完全符合突发的、搏斗过程中形成伤害的特点。如果
认定被告犯有故意杀人罪,从法医鉴定结论所描述的伤情上有很多不能解释的疑问,
不符合逻辑的情况,所以辩护人认为,这份法医鉴定结论同样不能充份证明被告人主
观上有杀人的故意。
(三)被告人的供述
辩护人同意控方在起诉书中所认定的相关事实:1、租车关系存在;2、行至被
告住处(不是骗至或强迫);3、因故发生口角。辩护人还要请法庭注意,应该通过全
面分析被告人在案发起因、经过、结果、手段以及与被害人关系上的陈述,综合分析
判断被告人的主观心态。
1、被告人记不清被害人身穿什么样的衣服,记不清为什么自己的手上有刀伤,记
不清向被害人划了多少刀、扎了多少刀,记不清从开始到结束时间,记不清什么时候
自己手中的刀不见了等,这些记不清表明:被告人是在一种极度冲动、紧张、恐惧、
失控的状态下实施的攻击行为,记不清当然是可以理解的;
2、被告人受到严重攻击。从被害人与被告人力量对比、从存在租车关系、从案发
现场在被告家,被告人应被害人的要求移开自己家的狗,从被告搬回啤酒箱、音箱等
这些情节上看,没有任何理由能说明被告人先攻击被害人,反而无法排除被害人先攻
击被告人的可能性;
3、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被告人与被害人曾经相识;
4、发现被害人死亡后,被告人逃避现实。刚满十八岁的孩子看到了自己不愿看到
的被害人的死亡,所以被告人下意识地运走尸体,而后不加掩饰的连车带尸抛弃在车
驱人往的高速路收费站边上,这充分说明被告人只是单纯地为了逃避现实,回避现实。
以上这些方面的陈述,符合逻辑,与相关证据印证,能够反映出被告人真实的主
观心态,表明被告人不具有杀人动机,不具有杀人的故意。
综上所述,在司法实践中,因民事纠分引起械斗而导致人死亡的,除有明显的杀
人故意外,一般都按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处罚。因为械斗的双方都是主动的,而且处于
互殴的运动状态,一时情急,失手,就可以造成对方死亡。特别是在分不清被告人是
故意杀人还是故意伤害的情况下,按故意伤害罪处理,是符合疑罪从无的精神的。公
诉机关出示的指控被告人故意杀人罪的证据,不能达到排除其它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所以不能认定被告人犯有故意杀人罪。
必须强调指出,在人们的意识中存在一种残留已久的错误而又顽固的传统观念,
这就是客观归罪的后果责任论,即只要刀伤无数、棍伤无数,只要造成严重后果,则
不问行为人主观上有无责任,都要从重从快处罚。这是封建主义的报复观念,是封建
意识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的冲突,是感情代替法律的表现。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必
须严格区分行为结果和行为性质这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才能准确地打击犯罪,维护
法律的正义与尊严。
二、被告人刚满18 周岁,应酌定对其减或从轻处罚
我国刑法规定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说明立法
考虑到了人对自己的行为辩认和控制能力是受年龄制约的。十八周岁是一个界限,但
它是一个社会年龄界限,是一种硬性规定。并非所有的达到十八周岁的人都能完全能
辩认和控制自己的行为能力,比如本案被告人在案发后所表现出紧张恐惧,足以说明
对自己行为的辩认能力是失控的。但是被告人已满十八周岁,不适用不满十八周岁应
当从轻或减轻的法定的量刑情节,可是由于被告人刚满十八岁不出一个月,因此,辩
护人以此作为量刑从轻或减经的酌定情节提出,请合议庭予以考虑。
三、被告人一贯表现好,且认罪态度好
据我们了解,村里和派出所对被告人的一贯表现都表示赞许,同时,被告到案后
如实地交待了自己的犯罪行为,积极配合司法机关追诉犯罪的活动,为此,请合议庭
在量刑时酌定参考。
再次恳请法庭对本案采取严肃、谨慎的态度,全面分析证据,对一个刚满十八岁
满脸稚气的孩子,正确适用法律。
辩护人: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韩嘉毅
二零零二年一月二十三日